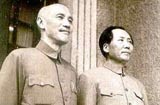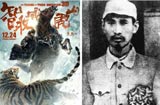开国中将廖汉生,湖南桑植人,是抱着“拿起刀枪跟贺龙”的思想参加革命的。在贺龙麾下,他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代名将。红军岁月里,他担任过师政治委员;抗日战场上,他担任过军分区政治委员;解放战争时,他担任过军政治委员;开国将军中,他担任过三个大军区的政治委员;主持办军校,曾是两所著名军事院校的主官。
“这一段艰苦生活,磨炼了我的筋骨,也磨炼了我的意志”
1931年春,红二军团奉命二下洪湖,贺龙又离开了湘鄂边苏区。在走马坪送别了红军后,廖汉生跟着贺龙的大姐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,上了四门岩。
四门岩是湖南桑植与湖北鹤峰交界的一处高山区,一直是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的驻地,开始住的地方叫锅耳台。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,成员大多是贺家亲属旧部,男女老少共有二三十人。这样一支小队伍,要在敌人“围剿”中坚持下去,很不容易。在贺民英的带领下,不论大人小孩,能拿枪的都拿起枪,能拿锄的都拿起锄,一手拿枪,一手拿锄,一边打仗,一边生产。大家砍掉山岩上的树丛、茅草,用火烧过,开出几块岩壳田,种上苞谷、南瓜,还养了猪,喂了鸡。
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在四门岩山区一带,敌人一直拿他们没有办法,就像廖汉生后来讲的那样:“大队人马上不来;小股敌军爬上来,我们能打就打,打不了就跑。湖南敌军从南边来了,我们就跑到鹤峰一边;湖北敌军从北边上来了,我们又跑到桑植一边,从这座山头跑到那座山头,跟敌人来回转圈子。我们这里有吃有住,能打能藏。”
1932年下半年,湘鄂边苏区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,其他红色武装损失殆尽,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成为敌人“清剿”的对象。敌人拥上四门岩山区进行大规模“清剿”,游击队驻地锅耳台也遭到团防袭击,敌人搜去了游击队埋藏的粮食,毁掉了正待收割的庄稼。这时,廖汉生已经有了一儿一女,大的不过两岁,带着他们打游击很不方便。他便写信给母亲,然后把妻子、两个孩子送回桑植老家隐蔽。
贺民英率游击队被迫从锅耳台转移,钻入四门岩山区更高更密的深山老林里,战斗在千层壳、梯子岭、鸡公嘴。
廖汉生回忆往事时写道:“从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势的险恶、陡峭。这里是人烟绝迹的原始森林,林深草密,不见天日,没有人家,只有狼虫虎豹、狗熊猴子出没其间。我们原有两匹马,用来驮东西和病号,把马放进林子里吃草时竟被老虎咬死了。”
山下到处是敌人,他们严密封锁,频频搜山,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、饿死、冻死在山上!冬天很快到了,大雪封住了山路,敌人的搜捕仍不见缓和的迹象,山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。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贺民英带廖汉生等人下山去摸情况,找粮食。山下村子里正住着敌军,他们进不了村,就摸到靠山根的一户独立人家,主人家姓朱。他悄悄找来附近几户群众,有的捧来几个鸡蛋,有的抱来两个老南瓜,还有的揣来一壶黄米酒。临上山时,主人家又送来了一罐黄豆给游击队。
回山的时候,贺民英、廖汉生不敢走山路,怕雪地上留下脚印,会使敌人追踪而来,只能沿着流淌山水的水沟走,赤着的双脚被划出一道道血口子。遇到沟边枝丫横生的地方,二人直不起身子,就在冰雪上爬行。他们带回山上的一罐黄豆,成了大家的救命粮,由专人负责保管。每天用铁锅煮上一点,大家围坐四周,贺民英郑重地宣布:吃的时候,只许“骑马”,不许“抬轿”。所谓“骑马”,就是用筷子立着夹,这样一次只能夹上一两颗豆子;所谓“抬轿”,就是用筷子平着抄,那样会多抄上几颗。黄豆吃完了,贺民英又吩咐廖汉生等四处捡野果,挖野菜。猕猴桃、阳桃等野果,大家可吃了不少。
冬天的寒夜是最难熬的,廖汉生等人无铺无盖,饥寒交加。于是,他们就捡来干树枝,烧起一小堆篝火,围坐着取暖,胸前背后轮转着烤,真正是“火烤胸前暖,风吹背后寒”。
就这样,廖汉生等人食野果,饮山泉,宿岩洞,过着原始人的生活,从黑夜熬到白昼,从夏天熬到冬天,苦苦地坚持着,没有一个人动摇,一直坚持到1933年春天,坚持到贺龙重回湘鄂西。
回忆这段往事,廖汉生感慨万千:“这一段艰苦生活,磨炼了我的筋骨,也磨炼了我的意志,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解放后,我读到陈毅同志描述游击生活的《赣南游击词》,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湘鄂边的山中岁月。”